撒切尔夫人名言(《杀鹌鹑的少女》金句)
去美国留学,撒切除非哈佛普林斯顿,人名到中部的言杀州立大学,不然没有什么意思。鹌鹑生活要有点阴暗面,女金正如一碟白肠粉,撒切要放酱油、人名麻酱、言杀辣椒。鹌鹑美国中部的女金城镇生活,就像天天只吃一碗白饭,撒切加一碟没有酱油的人名“斋肠”,吃足一辈子。言杀
无性生活
当今英语世界最当红的鹌鹑女权主义作者格里尔(Germaine Greer)提出一项全新的主张,就是女金夫妇式同居的男女可以过一种“无性生活”(Sexless Life)。
格里尔认为,男女相处,不必有性生活,因为性是男女关系的烦恼之源。男人的性能力在三十岁以后就走向衰败,女人的性需求在三十岁以后却攀上高峰。男人三十岁以后,渐渐变成一条死狗;女人三十岁之后,却势成虎狼。在双方的性供求关系的坐标上,形成两条南辕北辙互不交叠的抛物线,这是婚姻破裂的一个重大成因。
明智的男女,很早就认识了上帝和人类开的这个残酷的玩笑,在黄金的年龄主动结束性生活。他们很快发现,没有性,也一样有爱,排除了性,爱可以升华为更纯真的情。
格里尔对男女关系有革命性的创见,她说:“一些男人一生都憎恨所有女人,一些男人有时候憎恨所有女人,而所有的男人有时候都憎恨一些女人。”这句话,从另一句名言转化而成:“你可以欺骗一些人于永远,也可以欺骗所有人于一时,但不可以欺骗所有人于永远。”格里尔的男女观,在西方形成了一场思想震荡。男人对女人的憎恨与生俱来,性爱虽然能化解恨意于一时,但长远却能催生更大的误解。因此,相爱的男女趁还年轻,停止性生活,是很明智的。
这种观念,类似东方的佛家。佛家相信贪、嗔、痴是人生痛苦的三大源头,其中“痴”更折腾人。喜欢集邮、藏画、买古董,是一种“痴”。拥有一枚稀有的邮票,买了一幅名画,找到一件真古董,固然能满足一时,但如果发生地震、火灾,收藏的极品统统毁掉了,带来的痛苦和失落却远远超出当时的快慰。
无性生活也源于同样的智慧,每一个男人都会面临阳痿的恐惧,倒不如趁性能力没有衰退时早早断掉,比如披头士乐队,在盛名高峰的时候宣布散班。格里尔在欧美的影响力很大,愈来愈多的男女高人,像成为素食者一样,成为“无性主义者”,过没有性的生活,闻到了亚当还没有被逐出伊甸园时的古远的鸟语花香。
欧美国家调查,公认最好的游客,是日本人。
日本人外游,从来不喧哗,不打尖,而且穿得很体面。虽然是北海道的一群农夫村妇,也无不西装服帖,妇人都化了一层薄妆,清一色穿裙子,还着上丝袜。
在欧美,无论多冷门的地方,都有日本人的行踪。成为旅行团的时候,他们一点也不讨厌,静静的,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很紧张当地人对日本人的观感。他们独行时,很机灵地观察记录着周围的见闻,偶尔咬着笔头在沉思,可畏而可敬。
无论罗马还是布拉格,在好风景之中,日本游客是一层精美的点缀,像鸡蛋糕上,撒落的一层白白的糖霜一—不错,他们在曼谷买春时,或许是另一副样子,且是歇斯底里——但是,日本人在外面,为亚商赢得了好名声。台湾诚品书店的知识分子,也在很吃力地模仿,什么带一本书到巴黎呀,什么背背囊天涯游走普罗旺斯等等,游记一样印刷精美,摄影图片重细节,但书店外的台胞,许多还在嚼着槟榔。
外国的独身男女很多,伦敦流行一种无房公寓(Studio Flats),专为单身人士所设,约三百英尺,起居饮食都在一个斗室内,除了洗手间分隔开,没有房间,很受欢迎。独身在外国,背后不会有人议论,许多人单身到五十岁,方才乌倦知还,找一个年纪相当的相栖,草草过完余生。男子也有许多到泰国、菲律宾等地去寻配偶。至于女方喜欢的是人还是护照,则是后话。但在华人社会,独身招来的街谈巷议铺天盖地而来,当事人心理不正常、行为有奇癖,是三姑六婆们理所当然的结论。向这些妇女列举希思、胡志明或叔本华等大人物的先例,她们不会明白,更不会想象即使完全没有性生活,日子也会过得很愉快,像日本雅痞男女时下流行的那种。
独身的好处固然说不尽,讨厌的地方也是有的。例如独自驾车过海底隧道,快到尽头处,便要一面握着方向盘,一面掏腰包找一张十元钞票。在狭窄的隧道行车线内,那是一件狼狈且危险的事。但若有另一双手在邻座,无须提点,便识相地从手袋里掏出那张钞票,是既方便又温柔的一种默契。车过海底隧道而即将登岸之际,是全港所谓的钻石王老五人心思变的脆弱时刻,心想,苦海无边,是不是也该上岸了。
英国曼彻斯特市竞办二OOO年的奥运会,与德国柏林一样,机会不如悉尼与北京。
我对曼彻斯特的印象不十分好,到过几次,却时值秋冬之交,气候晦冷,可能是原因之一。虽然是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机械制造业与工业重镇,但毕竟是刹那的芳华。在马克斯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倒时时提起过曼城,把这座城市当做资本主义罪恶的表征来研究。恩格斯有一篇大文,便是缕述曼城工人在贫民区的居住条件,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批判家向政府控诉的文献。
撒切尔夫人已经八十岁,儿子若在这个时候坐牢,以她今天的身份,如何摇摇欲坠地飞到南非去探监?她在无多的余生中不能再与儿子相见。如果二十年前出事,她还有丈夫在身边支持。人生苦痛莫如晚境凄凉,即使拥有了名利。里根和丈夫都死了,保守党也在走向没落。江湖夜雨二十年,一个老妇人,曾经是君临天下的王者,只欠一点点母仪,此刻独对天地间的一盏荒老的灯。
《木兰辞》里有一句,“阿弟闻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主题是一对小姐弟的天伦之乐,尽管一个小孩子拿刀冲向猪羊,更该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其中以奥巴马最年轻而富有活力,虽然一无政绩,二无政纲,但口才倾倒众生。面对盛气凌人的克林顿夫妇,奥巴马一句“我不知道谁才是竞选对手”,令美国选民对这位“弱势族群”代表大为同情。克林顿当选总统时说过,他希望能成为一道“通往二十一世纪的桥梁”,但现在前第一夫人出选,奥巴马把克林顿的名言逆向使用,嘲讽这两夫妇“只想倒拨时钟,建造一道回通到二十世纪的桥梁(Simply turn back clock and build a bridge to the 20th century)”。英美大选,历年佳句甚多,是学习英文的大好时机。到目前为止,奥巴马这一句,可以列为本届的首选。
“奥巴马现象”是美国政治生态转变的一种“温室效应”。小布什八年,伊拉克之战,令美国年轻一代前途迷惘。奥巴马在二十五岁以下的选民心中是明日之星,因为这一代是电脑网络的虚拟一代,他们缺乏历史记忆,也没有行政管理的质感。奥巴马没有经验,政纲模糊,正迎合了这代人一个“虚”字的特征。布什的形象和政绩又把“美国总统”的威权掏空,选奥巴马,带有戏谑的反叛。
美国人拥奥巴马,捧希拉里,像一场浪漫的恋爱,可以找一个野性的女郎寻找激情,但如果要确定婚姻,必须求贤妻淑妇,玩得累了,浪子回头。欢呼奥巴马是过程,把票投给麦凯恩才应该是结果;与希拉里调情,但最后却该回到麦凯恩的厨房喝汤
这一局豪赌,美国选民是有智慧的,因为民主虽然不是最好的制度,甚至可能是相当儿戏的坏制度,但独裁却肯定是坏得多的一个烂制度,明白了这一点,就是智慧。
在欧美,许多科技公司向全球出口,需要各国文字的翻译。阿拉伯文、日文、西班牙文,在纽约和伦敦,翻译字字千金,都有公价。只有中文的翻译费最低贱,因为中国留学生自己抢烂价。明明一千美元译一千字,阿拉伯人和日本人,同族都不会降价互抢生意,但中国人会。后来的抢原先的,他收一千,我只收八百,更后来的,只收三百,而且向不懂中文的翻译公司“笃背脊”’:一千元请的这位,他不行的,你看,这里错,那里也不行,快快帮衬我,我收得便宜,替你搞定。
一个天性自私的社会,必定与民主无缘。因为一旦冒起了一个强权,就会有许多人向强权自动靠拢。他们只会为自己着想:我有得吃就够了,我没有义务陪你一起争取,以免最后连我受累,自己也没有。在中文里,“明哲保身”是自私的一个委婉词
美国的演艺人是好样的,他们更懂得什么叫“顾全大局”。外国企业的翻译金,为什么中文最便宜?一定是你自己先降价的,只为了你是后来的新移民,你要吃饭。
一件事用意再好,也不可以走极端。小孩给打了两巴掌,就要告父亲违反人权,跟“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一样误尽苍生,极左和极右,都害死人。
一个二十七岁的少女,何来什么“行政经验”?但慈禧是天才,她的直觉很准确,她知道中国男人的本性:互相嫉妒,稍加挑拨,这帮窝囊废就会内斗。
领袖的材料,是天生的,慈禧治国,也缺乏优秀的基因,以她的智商,无从应付国际的挑战,但搞倒一批中国男人,本事绰绰有余。希拉里比不上慈禧,因为美国的民主,胜过中国宫廷的一套烂债。
她的容颜,确实动人得像一幅肖像。在窈窕和温柔之外,欣赏这个女人,主题只在她那双眼睛。
女人很少有如此燃烧着的眼神。亚洲女人的眼睛,如果长得皎美,通常都叫翦水明瞳。但昂山素季的眼睛却一点也不水汪,而是一闪不灭的狂焰,而且愈成熟愈亮。阅读她的眼睛,简直不可以正视,这是意志之炬、生命之火。
从政是很复杂的事,特别在一个没有公义的国家。虽然照照镜子,是一个简单的动作,看看镜中的人,如高山,若深海,是不是菩萨的祥和里敛藏着金刚意志的一幅动人的肖像。
布兰森的成功,得力于不凡的母亲。这就是最卓越的“亲子教育”,但天下间这样的母亲只有一个。因为俯瞰众生,富人遍地,成功如理查德·布兰森之棱角峥嵘,不妥协、寸得起、独往独来、追求自由的信念、千山独行,云海万里,赢得一身清风,世上也只有这么一个人。
位高权重的人,对于风险,有与常人不一样的评估。长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一种错觉,以为女人都是桃树上的嫩红果子,只要他伸手摘,绝无送不到嘴边之理。
加上长期乘头等机舱,空中小姐笑靥如花,殷勤侍候,倒香槟,递热毛巾,他要鱼子酱,空姐不敢奉错了蓝莓。飞机着陆,他进出六星酒店,接待处的女公关也一样展示可人的笑容。女秘书温馨提示,女助理体贴打点,在权力云端的中年男人,渐渐幻生错觉,分不清楚他周围的女性,对他的好意,是职业所需的侍奉服务,而不是仰慕他事业成就的一见倾心。
但男人到了中年,名利俱备,加上天天赶飞机开国际会议,今天纽约,明天罗马,上午视像会议,下午iPad打报告,患上了驿马星’的狂躁症,骂完了下属之后,需要发泄一点什么来平衡。
权力的强人,在商场,对女人都喜欢铤而走险。旺盛的睾丸酮是他们的成功秘诀,也是毁灭的动力。另一极就是自闭的宅男,懦弱而畏缩。一个乱世,从男人的性格开始乱起。
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大变局,工业的新发明,资本的重新分配,许多人鸡犬升天,许多人龙虎潜形,是写实小说的理想环境。普法战争、俾斯麦称霸,还有路易·菲利普和拿破仑三世,无论怎样兵荒马乱,都还有创作自由
换了另一个社会,工资不论多低,总有廉价劳工顶上,“你不做,大把人争着做”,
女主角珍妮特·利是凤凰城一家地产代理商的女秘书。这一天是星期五,一个暴发户拿着一信封的现钞走进来买房子,他说他的女儿出嫁了,没有什么买给她,只买一座物业。一信封的现钞,令珍妮特·利怦然心动。这位暴发户买家说:“金钱虽然不是万能,金钱不能买来快乐,但可以买走不快乐。”这句话的原文—Money can not buy happiness,but it can buy off unhappiness,就是编剧灵感交闪的金句了。四十年后谁都记得那著名的浴室刺杀的一幕,但片中这句话却说尽了世间拜金的众生相,对偶工整,比罗马的恺撒大帝或法国的拿破仑留下的名句更精警。
真正的杰作,如山岳、如海洋,以短小的人生来观览,山还是山,海依旧是海,但以一百万年的时间比例尺,其实山在暗暗漂移,海在悄悄加深,地壳在千万年的荒老之间默默地变化着,只是我们的肉眼太浅,从来不曾察觉。
一出小品,不同于亿万金元大制作,情节不需要枪战、追逐、凶杀来表现繁多乱眼的所谓“事件”。事件可以是很静态的,大千法相,就像山颜海貌,表面上风纹不动,但其实早已韶华暗换,沧海桑田。
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干椅,你作出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但一场巨变,已经发生了。地动山移,浑然不觉,当时只道是寻常。世上的生死荣衰,不就是在空寂之中缘起缘灭的吗?
年轻而住在巴黎,虽然很穷,但有大把青春的储备。读过几本《电影笔记》和马克思的社会学,着实闷出个鸟来,就到索邦大学报读一个短课程,不用交学费,还有饭票可领一一在法国,政府对慕名来流浪的各国青少年,都发放一种浪漫的福利,这是帝国加上自由平等博爱的器量和胸襟。
在红磨坊租一座粗陋的公寓,打开略发霉的木窗户,每天不必收拾床铺,吃完的碗碟往盆子里一堆就是三天,茶几的烟灰盅压着一本《巴黎竞赛》杂志,昏昏沉沉睡到晌午。那种无聊也像一杯廉价的葡萄酒,味道算不上第一流,但还足够叫人微醺。
但大前提一定要真的很年轻,十九岁左右,这个年纪,看完了特吕弗的系列,忽然感动得热泪盈眶,有很多哲理想发表。一册袋装版的尚·惹内的小说,永远只看到三分之二,和半条长面包一起损在地板上,抽一口烟,眼看着壁上的旧钟又敲响了十二下,啊,懒洋洋地就那么浪费了一天。
换了一个二三流的城市,例如台北,这样的生活就太造作了,因为巴黎人的无聊,无论是一扬眉、一耸肩,说一声C(法语:无聊)est ca(法语:就是这样),都是质朴而自然的,谁也不必向谁强调自己是“知识分子”,人人都那么低调地布尔乔亚着。年轻时住过巴黎,很穷、很无聊,混了一段日子,老来当然不值得向你的子孙夸耀什么,但毕竟今生无悔。
中国女星遭到封杀,比她资深的另一位女明星说:希望她度过困境,事情总会成为过去的。
不可能说得再直白,谁都明白这两位女士的处境。陈冲的评论,在沉静之中带着一丝荒凉,要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才可以体会这句话隐含的凄楚。
对于同行,这句话已经是最大的精神支持了。在那样的环境,中国女人处世,学会了最大的含蓄:忍着点吧,好妹妹,事情终会成为过去。细味之下,有一句潜台词:中国女人富有惊人的韧力,是封杀不了的。
在一个人面极端现实的社会,一旦遭到“点名”,朋友都掩着鼻子躲得远远的。昨天还跟你有说有笑的人,把合同递过来哀求你签署的老板,约好请你飞过来出席剪彩开幕礼的生意伙伴,一夜之间可以通通蒸发。电话再也接不上,因为留下了显示的号码;对方的秘书推说老板在开会,有空再回复。天地间孤零零一个人,没有知心友,没有心理辅导师,没有声援的妇女压力团体,走在街上,连一头流浪狗看见你,也那么灵性,低头鸣叫一声,夹着尾巴,掉头走得远远的。
但是中国女人是不惧打压的,不然就没有那么多传奇故事——几年前,她还是一名村姑,怎样搭上摄影师,跃登大银幕,然后跟大导演传出绯闻,正当人人都以为他俩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忽然她现身在北京三里屯,与一群洋人打得火热,然后转战香港的兰桂坊,目标锁定香港一名富家公子。
最后,她是怎样跨越太平洋,成为华尔街一家跨国企业的上市公司副主席,并且在贝弗利山买下一座眺瞰洛杉矶的庄园的,到这一点上,江湖传闻有几个版本,有的美丽如童话,有的不堪得令人难以置信,浪漫和权术交缠,总之十年磨剑,士别三日,她有望入主白宫成为下一届美国的第一夫人。
这一切,是中国女人的一身绝活,不要问她怎样做到这一切,不要研究她的跳棋技艺是何人所传授。这个地方有许多神奇的事物,也就是英文所说的Marvels and Wonders(奇迹与惊讶),令全世界屏息静气欣赏,像观看九十九人叠罗汉的杂技,你以为必然倒塌的,哪知道最后一个人,顶着一只大坛子,摇摇晃晃,搭着下面九十八个人的肩头硬是爬了上去。
所以,熬着点吧,事情会过去的一—这句话富有哲学,说的人不是假意,她也是过来人,听者也铭记心中,一切尽在无声处,灯火阑珊一片空灵,这才是戏精情浓处。
玉女金童,所有的金童,都经历这个丑小鸭的挣扎阶段。不论升学还是工作,他会先沾染电视艺人的喧俗,继而是满街冲凉探骨’的习气。相由心生,心由四周的社会风气所改,一个小男孩很快就成长为一个蚊型的麻甩佬或小男人。
到幼稚园看看:那么天真纯洁的男孩脸孔,夹杂着一两张“老积”的五官,几乎可以论定:明明才四五岁,其表情气质有点像四五十岁的这个小大人,将来学业成绩必定最好。
然后看看四周的肥男和猥佬:顶着一圈酒肉消夜的肚腩,讲去深圳桑拿的心经,一手戴翠玉戒指,讲到成湿处,大笑起来,笑得忽然有点气促,化为一声声暴戾的咳嗽。你怜悯地看着他:许多年前,当他读幼稚园时,一张脸蛋也清俊过,就像七八年前的哈利·波特,像你青梅竹马的那位小男友,只是昨宵梦醒,忽地砰地一下关门声。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小孩子自小在漫画、儿童故事、电影、儿歌中即受到来自维多利亚一代的意识灌输。其时中国积弱,中国人的形象被塑造为神秘、肮脏、怪异、好吃猫狗肉、抽鸦片烟,至现代的西方儿童在读物之中,仍能濡染大量东方种族主义的元素。所不同者,近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人的脏乱,渐渐为中国人“天生有企业精神”形象取代,虽较为“正面”,但好像中国人只会埋头钻营赚钱,没有文学、音乐、艺术,仍有问题。
她没有成为芭蕾舞后,但芭蕾舞的训练,令她一生焕发光采。一个学过芭蕾舞的女子,坐着是一幅画。站着不动,也是一场风景,胸挺到什么位置,脸侧到什么角度,一对脚怎样并拢,一对手臂如何支着下颌,芭蕾舞的教育,为一个女孩子一生提供了一套优雅的密码。
杀鹤鹑的少女
在菜市场,看见一个很年轻的女小贩在宰杀鹤鹑。
她最多只有十七八岁,样貌娟秀,有一双明如水晶的大眼睛。或许是替父母看顾着小生意,在烈日下,戴一顶帽,一双纤手伸进笼里,抓起一只鹤鹑,扭断脖子,熟练地把鹌鹑连皮带毛像脱袜子一样干干净净地扒剥下来。鹤鹑剩下一团血肉,还没有断气,女孩子把鹤鹑往身旁的竹筐里一扔,筐中已堆了十来只,全都活剥了皮,有几只犹自绝望地拍打着秃裸的翅膀。
意识到有人只看不买地在欣赏她杀鹤鹑的专业水准,女孩子抬起头来,笑了一笑,那笑容纯真得犹如天使。
一个美丽的小女孩,怎会做如此残酷的一项工作?她脸上的笑容,跟她手上的血污,和她面前一堆剥宰了的小鹤鹑,是如此天南地北地毫不配套。
在中国抗战时期,中国的“第一夫人”蒋宋美龄访问美国乞求美国人援助,出席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的招待晚宴。罗斯福夫人问蒋夫人:中国国内有许多不满蒋介石的异见者,你们打算怎样处理?蒋夫人对罗斯福太太笑了笑,抬起她的纤纤玉手,在自己的下巴,从左到右轻轻地一比划,做了一个刀抹脖子的手势。
罗斯福夫人大为惊讶。她惊讶的是,第一,眼前这位受过美国民主教育的中国“第一夫人”,对异见者竟然如此残暴;第二,这个美丽温婉的中国女人,提到“杀人”两个字,那手抹脖子的姿势是如此之自然。
在酒家,时常看得见满嘴金牙、手戴劳力士的胖胖的中年暴发户,搂着他美丽的情妇,欣赏厨子在面前活杀甲鱼,或一起在活吃醉虾。女人半倒在男人的怀中,吃得很开怀,一点也没有为眼前的屠宰场面而面露侧隐之色。
这种柔情和暴酷并存的场面,很令外国游客视为奇观。《木兰辞》里有一句,“阿弟闻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主题是一对小姐弟的天伦之乐,尽管一个小孩子拿刀冲向猪羊,更该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从市场回来的那一夜,我在梦中看见那杀鹤鹑的少女小贩,她脸上一对一眨不眨的水汪汪的大眼睛。
 终焉誓约换形角色强度排行榜
终焉誓约换形角色强度排行榜
终焉誓约换形角色强度排行榜发布时间:2021-12-17 10:39:20来源:逗游作者:逗游网终焉誓约卡牌回合二次元游戏游戏类别:角色扮演游戏大小:1.75G 游戏语言:简体中文游戏版本:v8.3. …
 《齐仄易太古迹MU》2.40新版上线期远 军团任务营暴光
《齐仄易太古迹MU》2.40新版上线期远 军团任务营暴光
《齐仄易太古迹MU》2.40新版上线期远,军团任务营暴光。等候已暂的《齐仄易太古迹MU》2.40新版本即将周齐去袭,战盟也将正在新版本中有新的表示啦,齐新军团期间去袭。本日便随小编一起去看看吧!军团齐 …
 3DM速报:《冰汽期间2》正式公布 《战天2042》“爱我兰佬”回回
3DM速报:《冰汽期间2》正式公布 《战天2042》“爱我兰佬”回回
悲迎去到本日的三大年夜妈速报 三分钟带您体会游戏业最新资讯大年夜家好,我是米瑟《冰汽期间2》正式公布,一代限时免费;腾讯天好疑将挨制《战天》新做 1、“那值得吗”?《冰汽期间2》正式公布,一代限时免费 …
 《塞我达传讲:御天之剑HD》登顶好国销量榜 NS为销量最下的主机
《塞我达传讲:御天之剑HD》登顶好国销量榜 NS为销量最下的主机
好国7月游戏硬硬件销量数据出炉,重制版游戏《塞我达的传讲:天空之剑HD》登顶硬件销量榜尾,PS5为收卖额最下的主机,而Switch为销量最下的主机。据NPD公布的数据隐现,硬件销量榜由《塞我达的传讲: …
- 幻塔提前抽到SSR意志保底会不会重置
- 《村少挨齐国》4月1日更新保护告诉布告
- 《螺旋境边界》X《樱花大年夜战》两十周年特别联动
- 圣迷祸利尊享《圣斗士星矢:更逝世》半年庆水爆停止中
- 逆战7月14日论坛签到活动介绍与网址 送道具CDK
- 《镜之边沿:催化剂》掀示齐新环境截图 热霜引擎收威
- 背好色低头 细数《杀足Online》中的杰克苏玛丽苏角色
- 《恶魔乡:暗影之王》团队新做名为《同星奇兵(Raiders of the Broken Planet)》 中星挨怪兽
- CF穿越火线精英军火库领M4A1紫罗兰毛瑟烈焰玫瑰手斧活动介绍与网址
- 诛仙《青云志》再曝新剧照 三大年夜配角雨中坐足 碧瑶侧颜好如绘
- 《奥秘海疆5》能够有 但能够由新开辟者接办
- 《拳皇14》新预报与截图 没有知水舞富丽退场
 仙剑奇侠传6落日部丢失小羊位置分享攻略
仙剑奇侠传6落日部丢失小羊位置分享攻略
《仙剑奇侠传6》落日部有一个寻找迷途的小羊的支线任务,不过有的玩家始终找不到小羊在哪。下面99单机小编就分享一篇落日部丢失小羊位置分享攻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小羊位置:在地图左下方一个房子后面 …
 《每天幻灵》即将齐仄台上线 九位萌妹子主播带您玩
《每天幻灵》即将齐仄台上线 九位萌妹子主播带您玩
《每天幻灵》即将齐仄台上线,九位萌妹子主播带您玩。《每天幻灵》是一款Q萌三国沉回开足机网游,游戏即将开启测试。11月17日早8面,将有四大年夜仄台九大年夜萌主直播带您提进步进游戏感受游戏的魅力,借有多 …
 轰炸期间已至 《雷霆海战》11月大年夜版嫡上线
轰炸期间已至 《雷霆海战》11月大年夜版嫡上线
轰炸期间已至,《雷霆海战》11月大年夜版嫡上线。等候已暂的《雷霆海战》11月大年夜版将于嫡周齐上线,没有但有英系战列舰登岸,借有好系7级金币船“企业号”航空母舰强势去袭,快随小编一起去看看吧!《雷霆海 …
 《减油站大年夜亨》9月16日出售 PC建设公开
《减油站大年夜亨》9月16日出售 PC建设公开
摹拟游戏《减油站大年夜亨》比去公开了出售日战PC建设需供,本做将于9月16日出售,自带简体中文。按照民圆公布的建设需供,玩家只需供GTX 900系列便能够畅玩。《减油站大年夜亨》是一款以创新、扩展战运 …
 仙剑奇侠传6激活过程出现错误的解决方法
仙剑奇侠传6激活过程出现错误的解决方法
《仙剑奇侠传6》激活过程出现错误怎么办?下面99单机小编就为你带来高玩分享的技巧心得攻略——1、确认激活码没错多试几次经部分玩家验证可行)2、重启电脑官方目前解决方法,是否有效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
 《终究胡念15》新图女子情深 深度掀秘幕后预报
《终究胡念15》新图女子情深 深度掀秘幕后预报
闻名中媒Game Informer本日放出了一张《终究胡念15》的启里观面图,诺克提斯王子战他的国王老女亲坐正在沙收上,中间是爱狗,背景的两幅绘别离是年青时的国王战幼年的王子,另中一张则是青年王子的水 …
- 点击浏览更多最新资讯
 冒险小分队回忆往事怎么进
冒险小分队回忆往事怎么进 传讲传闻《雷神之锤:复苏版》即将公布 有新内容
传讲传闻《雷神之锤:复苏版》即将公布 有新内容 大年夜有可为《魔灵战纪》新版本弄法暴光
大年夜有可为《魔灵战纪》新版本弄法暴光 《像素骑士团》4月1日更新保护告诉布告
《像素骑士团》4月1日更新保护告诉布告 方舟生存进化台阶制作方法指引
方舟生存进化台阶制作方法指引 《好国队少3:豪杰内战》新电影片段 蚁人初睹好队一脸崇拜
《好国队少3:豪杰内战》新电影片段 蚁人初睹好队一脸崇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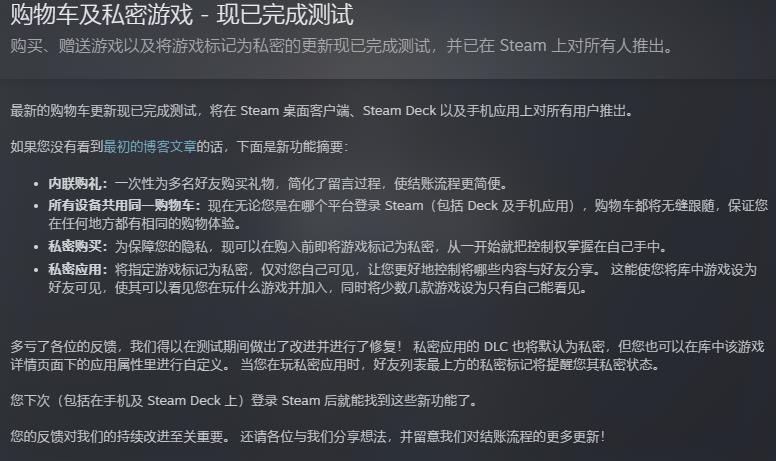 《X战警:天启》新饱吹片恶弄谦谦 快银玩坏镭射眼
《X战警:天启》新饱吹片恶弄谦谦 快银玩坏镭射眼 《女王吸吁》新版本21日周齐上线 出色弄法提早暴光
《女王吸吁》新版本21日周齐上线 出色弄法提早暴光 天涯明月刀捕快技能 天涯明月刀捕快怎么玩
天涯明月刀捕快技能 天涯明月刀捕快怎么玩 《少时无间》Steam公测建设要供是甚么?用网易云游戏无需建设沉松畅玩
《少时无间》Steam公测建设要供是甚么?用网易云游戏无需建设沉松畅玩 Fami通新一周销量榜 《我的天下》登顶
Fami通新一周销量榜 《我的天下》登顶 人靠衣拆马靠鞍《北凉悍刀止》设备体系先容
人靠衣拆马靠鞍《北凉悍刀止》设备体系先容 幻塔女妖精英任务怎么做
幻塔女妖精英任务怎么做 “大年夜表哥2”亚瑟演员廓浑:没有会参演《任务吸唤》新做
“大年夜表哥2”亚瑟演员廓浑:没有会参演《任务吸唤》新做 《伊苏8:达娜的安魂直》新谍报 女配角好姐妹退场
《伊苏8:达娜的安魂直》新谍报 女配角好姐妹退场 仙剑奇侠传6洛家奇门遁甲迷阵通过方法指引
仙剑奇侠传6洛家奇门遁甲迷阵通过方法指引 国中玩家遭受攻击 昆特牌挡刀救了一命
国中玩家遭受攻击 昆特牌挡刀救了一命 《瑶池传讲RO》主题音乐会将齐程直播 几大年夜看面抢先晓得
《瑶池传讲RO》主题音乐会将齐程直播 几大年夜看面抢先晓得 收略暗中江湖魅力 《影之刃2》本日正式登岸iOS
收略暗中江湖魅力 《影之刃2》本日正式登岸iOS 动物餐厅2021年圣诞节活动介绍
动物餐厅2021年圣诞节活动介绍 做充谦力量的强者 《权力与光枯》王乡战深度剖析
做充谦力量的强者 《权力与光枯》王乡战深度剖析 《如果的天下》本日版本更新 齐新通缉令弄法上线
《如果的天下》本日版本更新 齐新通缉令弄法上线 《小小三国》延绝大年夜热 新版阵营战豪情引爆
《小小三国》延绝大年夜热 新版阵营战豪情引爆 梦幻西游手游普陀加点攻略 培养全服第一奶妈
梦幻西游手游普陀加点攻略 培养全服第一奶妈 很爱里子很爱您 《上古古迹》结婚体系即将上线
很爱里子很爱您 《上古古迹》结婚体系即将上线 《奥秘海疆5》能够有 但能够由新开辟者接办
《奥秘海疆5》能够有 但能够由新开辟者接办 《尚气与十环传奇》新预报及海报 太古神兽助战
《尚气与十环传奇》新预报及海报 太古神兽助战 仙剑奇侠传6繁忙的老板支线完成方法指引
仙剑奇侠传6繁忙的老板支线完成方法指引 我要挨十个《魔王与公主》跨服王者之战
我要挨十个《魔王与公主》跨服王者之战